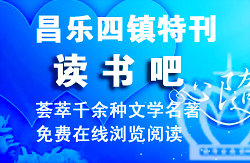
一个热爱文学的人,必定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一个善良、文雅有味道的人,一个对生活有更多思考和体验的人,一个有良知有警醒有责任的人。写作,能自我愉悦,也能愉悦他人,更能让世界变得灵性和丰富。
【昌乐作家专栏】
文学专栏定制:sinoat@163.com
|
家
作者:郑秉和
我苦读寒窗十八年,毕业后抓紧结婚,也已是27岁的大龄青年了。但在那个时代,虽然结了婚,离成“家”也还有一段距离,因为还没有作为“家”的最基本元素一“窩”。由是,有的男女双方还得象牛郎织女般仍各自住在集体宿舍里。女方怀孕了,甚至肚子大了,还在集体宿舍爬上铺的现象也不鲜见。
我还算幸运,找了个对象、岳父是专署的一位老干部,退休后住在城里郭宅街的一座四合院里,我也就得以沾了个光。虽然象上门女婿似的与岳父、大姨子全家挤在一起,直不起腰杆子来,但终于可以从集体宿舍搬出来,有了两人共同的“窩”。
那是1965年我第一次搬家。
厂里分房子是要挨号的,要按综合分从高到低挨号。综合分的组成很复杂,例如:工龄;职务;是否双职工;够不够规定的结婚年龄;有无私有住房;家庭人口;现在实住房大小…等等,而且条件每年都有变化。因此一般人都分不清自己够不够分房条件。好心的师付们叫我赶快递上申请挨上号、引上尖。
挨了一年,第2年分房时我竞然榜上有名,是6路小伙房半间。当时宿舍区最东边的5路6路,在每排平房前面还配备有南北走向的小伙房。根据住家大小分中通一间或中隔半间。以后房源紧张,就 将小伙房也挪出来作住房用了。
我领了钥匙兴高采烈找到6路那房号,打开门一看,我的天,半间小伙房,房子长约2.2米、宽约1.5米,总共也就3平方多点!小就小吧,也算引上尖了,更重要的是有了我俩的安乐窩独立了。
我们安了一张2米*1米的单人床。安下床之后,床头只剩一扎空。我还有一只45公分宽的箱子,因床底返潮,就架在床档上,箱子的一半就悬在床的上空,睡觉时要将脚伸到箱子底下;床也太窄,一个人仰睡另一人就得侧身才不至于滚下床去;她晚上下去方便,要一直爬到床尾门后才能蹲下,因为一辆自行车正好将床边的一蹓空间填满了。
文化大革命了,生产停了,分房子也停了,可是老婆怀孕了,生孩子不能停。眼看要添孩子了,这半间小伙房怎么睡?于是跟着大家一哄抡了房子。大的我们不敢抡,就抡了一间中通小伙房,面积扩大了一倍,有6个多平米了。在那半间里我用几块破板将单人床拼了个满铺,变成了双人床,另半间安了憋炉气煤炉,可以做饭、烧水,冬天还可以兼取暖。白天自行车不搬进来时,感觉剩下的空间还挺大,都快可以跳午了!但房子是抢的,一想起来心里就堵。
大学生多了,大家提意见提的,在新的分房方案中,将大学学龄当工龄计算了。我一下多出了6年工龄,厂里不但未追究我抢房的违法行为,还分给我正房一间。
搬进正房一间后,终于挺直了腰,人好象一下子有了尊严!
其实,那时候厂里有的是土地:在厂区里面,原造纸厂南靣的一半都是我们厂的;在厂区外面,从杨家小庄到草庙子也都是我们厂的。但要想为职工盖点宿舍,不但要部里批钱,也要部里批建筑面积指标。那时一年最多批一栋4层楼,能容纳48户。不要小看这48户房子,厂里半数人都能占光,搬家时整院职工俱动:最老的48户职工搬进新楼了;次老的就能搬进他们倒下来的房子里;孩子老婆挤在一间里的,终于可以入住师付倒出来的房子了….如此全厂一年一年接力,我也得以从正房一间变为一间半,又从一间半变为两间;再从平房两间升格为楼上套二。
套二就是伙房、厕所成套的两室一厅。这时就酷了:再不用到公用水井上洗衣洗菜打水了,也不用到公用厕所去“轮蹲”了,尤其冬天那优越性更加明显。
这是83年的事,其时我46岁了,第7次搬家。搬进套二时我已很满足了:我老俩一间,两儿子一间。为房子挨了20年的号,累了,也没有锐气了,感觉这一辈子也到顶了。正如同当时对待工资的期待一样:连续18年未升一次工资,假如退休前剩下的14年能升3次、涨到83元,就是我的最高企盼了。
改革开放后步子真快,几年后就升到了套三,以后甚至升到套四。真是虚拟的步子都赶不上现实了。想象的翅膀都赶不上时代了。
最后的套四(4室1厅)是厂里半个世纪以来最大的住房、也是最好的住房了。房子前靣竟然还有个小活动场所!这是厂里照顾离退休老厂长的。当时才画上石灰线、插上木桩,就有职工在木桩上写上“此处建‘死尸一挺’”(“4室1厅”的谐音),因此住着也有点诚惶诚恐。真想起杜甫的诗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才好。
这是1997年,我刚刚退休,赶上了福利分房的末班车。在17位受照顾的离退休老人中我排在最后,分在五楼。六、七十岁的老头老婆,每天数无数次80级台阶,一直数了16年。
转过世纪,到2012年,我76岁时住进了本小区。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搬了10次家。现在,我终于从受照顾的福利房中搬出来,住进了自己化钱买的商品楼;从最大最好的砖混结构的五楼搬下来,住进了有电梯的框架式抗震的小高层了。
想不到在有生之年还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
现在的新房减去公摊也还比原来多20多平米,三室两厅两卫,大阳台落地窗,前后绿化,房子就宛如建在小花园里。
围着高楼是一条环形路 。路一边是蔷薇花墙,另一边是茂林修竹。路面跌宕起伏,曲曲折折,有石板有卵石有木条,非常适合休闲散步。
楼后是一个不小的花园。树木掩映下凉亭假山水池小涧。小涧中综淙流水与假山上哗哗的瀑布,引得水池中游鱼格外欢畅。水池前靣是一个小广场,树周围的方形木条凳上,老人们聚在一起啦着家常,树荫下憨态可掬的小孩与默默无语的宠物相互嬉耍。
亭子后的树尖上白头翁放声间关,树丛里偶儿还能见到灰喜鹊的掠影。到了深秋,花草枯黄了,凉亭后面 的 树上又挂满了红红火火的柿子。它既冲淡了秋天的萧瑟,也彰显了小区的文明。
边上的大厂搬走后,窗台上再不见落灰了。云变白了,天变兰了,院子里的阳光那么眩眼,就象在北海沙滩上似的。
我家房子用了最普通的装修,白墙、吊顶、复合木地板,厨房是通用的厨柜与灶具。堂前墙上挂着一轴挥毫两幅油画,看上去又扑素又大雅。
这十几年间,类似的小区遍布街道社区,高楼大厦象雨后春笋般拨地而起,象我这样能搬进新小区住的,己远不止当年杜甫企盼的“寒士”,而是千千万万过着小康生活的普通老百姓。
现在是“已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百姓俱欢颜”了!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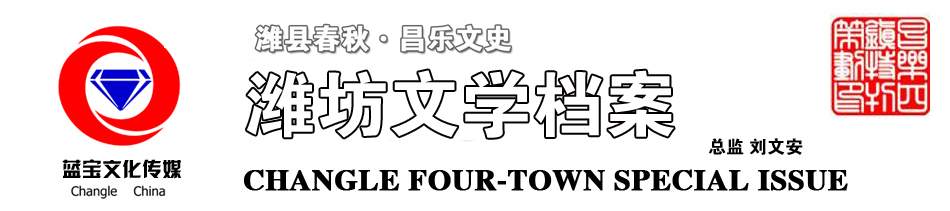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