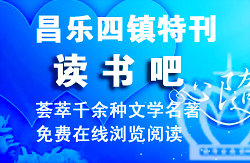
一个热爱文学的人,必定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一个善良、文雅有味道的人,一个对生活有更多思考和体验的人,一个有良知有警醒有责任的人。写作,能自我愉悦,也能愉悦他人,更能让世界变得灵性和丰富。
【昌乐作家专栏】
文学专栏定制:sinoat@163.com
|
森林里的“漫散古道”
作者:张国柱
从临朐五井镇上五井村向西,过去有一条小道,被称作“漫散古道”(也有的叫“漫萨古道”),经开井村、白洋口、北道村、岸青村、杨集村、洞顶村等,通达淄川一带,是当地蚕农到淄川销售蚕茧的重要道路。
关于“漫散”的范围,网上的资料说是大体指青州仰天山北侧的一片30多平方公里的无人居住区域,是北道小流域、孙王小流域、岸青小流域和西股流域水系的发源地。至于“漫散”一词的由来,一直也没有查阅到明确的记载。估计这是当地村民对这一带地质结构散而杂乱的一种口语称呼吧!在青州王坟镇北道村西约1公里的古道边,有一块碑,为“修路碑记”,大体记载了民国7年重修古道的事,但碑文没提及“漫散古道”四字。
2009年10月5日至7日,与三个户外朋友相约,徒步穿行了漫散古道(临朐青州段),行走大体路线如下:从五井镇上五井村起步,经小刘村,天井岭村,白洋口村,石道人山,北道村,仰天山北麓,双崮顶,岸青村,杨集,到洞顶,然后经黄花坡村,沿黄花溪而出。一路林木葳蕤,荫翳蔽日,堪称是森林里的“漫散古道”,归后随记。
从天井村到北道村
天井村是个大村,200多户人家。村内路、屋、墙、舍多以石构成。路上的青石板,已经踩磨得光滑可鉴,其岁月足可见久。石墙、石屋、石阶、石凳、石辗、石磨,朴厚且沧桑着,展示着山中小村的悠悠风貌。村中多树,杨柳榆松,品类多多,整个村子就隐在绿树中。更多的是果木,以柿子、山楂、山杏等居多。
老柿树生得极为生猛,在屋角,在路边,在一切可想可不想的地方,突然就闪出一树金黄来。高大的树干,虬枝苍劲,柿也挂得威风,或高挑在上,或低匍在下,连同周边的山势也生动起来。柿树多已落叶,在干干的枝上,挑满澄黄的柿子。山楂熟透了,红得耀眼,任那青碧的叶如何繁茂,也压不下它的红艳来。还有枣,红青不一,各展其颜,尽显酸甜。
“漫散古道”就在村西北边,现在仅余300多米的一段古道,宽处约2米有余,窄处最多米许。路面用厚达20厘米的青石板铺就,中间还利用了一些山上裸露的原石。路沿参差不齐,石与石之间,缝隙大小不一,均已积满泥土,这泥土中又生出密密的草来,时草已变黄,如一条条苍黄的线,把路面依石形分割,古老中显着奇壮,苍苍中缀着灵巧。
古道往前并入了新修的水泥路。再前行,就是白洋口村了。据向当地村民打听,原古道,从此分叉。一路往西到淄川,就是所谓的“漫散古道”,谓“蚕道”;另一路从此向南,到临沂,谓“山道”,向北经五里,西到临淄谓“商道”;东去青州府谓“官道”。
而现在,白洋口村往西的原古道,已经被修铺一新,与“仰天山路”并为一路,西南方前行4公里许,即是北道村。在白洋口的午餐后,小憩片刻,继续前行。因为仰天山路是柏油路,沿此路去北道村,虽然便捷,却因平整,少了些户外徒步的乐趣,于是决定稍稍改变一下路线,取道白洋村、上白洋村,从上白洋村翻石道人山,到北道村。
去白洋村的路沿溪而修,近三米宽的水泥路。路边有柿树、杨树、槐树、柏树,还有桑树。那些粗粗的桑树明显是古桑,应有上百年树龄,叶极小,枝极乱。虽远不及现在经过改良的矮株桑树的枝纤叶大更加经济实用,但它们默默地用自己的苍桑,告诉我们这里古时蚕桑经济的兴旺与发达,以及“漫散古道”作为桑蚕古道的充足理由。
林果是山里人的钱袋子,白洋村里自然也有果品加工厂。这个时节,加工山楂最多。远远的就有醇厚的酸夹着甜飘过来,就像这山里的日子,朴实厚重,酸甜交迭,而过后留下的,却是沁人的果香。穿村而过,就是上白洋村了,已经可以从房间树隙看到南面的石道人山了。高峻的山头,八堆石头,成道人模样,依在山上。据说,山上共有九位道人,其中有一位是躺在地下的。
从上白洋村内一条夹在树林中的小路向南,就可登石道人山了。起始,路还很好行,虽一路向上,但尚有迹可循。但渐行渐难,待翻过几道梯田石岭,已难寻路,眼前全是人迹不见的原生态丛林,高树低灌,杂木野藤,荆棘交织,藤萝纠缠,绕若迷宫,眼见石道人山就在前面不远处,却再也无法前行。
于是我们决定绕行到西边的松林间,沿松林边缘向石道人山靠近。好容易攀到西边松林中,却发现这片松林更加难行。松树极密,明显是人工植育而向,树龄不在50年之下,横成排,纵成行,绕山而生,青绿苍翠,枝干相交。人在林中,俨然入了迷宫,上看不见天,下看不见谷,几乎找不到方向。只好又折回,在密林艰难穿行,迂回了一个多小时,终于来到林子的边缘,视线豁然一亮,竟然从林子间找到了一条似路非路的可循之踪,向东南行十五分钟后,终于到了石道人山之下。
石道人山,由八、九根硕大的石柱组成。石柱直径不一,形状不一。宽处约三米多、窄处仅1米余。高的十多米,矮的七八米,或聚或散,或依或离,东西方向排列在峰顶上,雄伟奇崛,浑然天成。近观,这些石柱可谓大矣!累累巨石,排列成一条线,好像远古时代高大建筑残存的墙垣,或者是坍塌的梁柱。远看,才如一排石人静立。这些石头其实是喀斯特地貌形成的巨型石柱,石多迭积,石质细腻,又经了千年风雨的冲刷,石块顶面大多整洁光滑。再看柱身,风雨不至处,棱角分明。石柱的顶上,石块左突右出,如锯齿,似狼牙,参差错落,酷似道士头上的道冠,而石柱上的石头纹理,又酷似道服。想来,石道人山大约由此得名吧!下山后到村中访问才知,当地有“八仙化石人”“馋嘴道人偷食煎饼糊”等诸多与石道人山相关的传说。
石道人山上植被丰盛。且不说满山的松柏荆棘,也不说山腰的枣树、柿树、桃树、杏树,只看茂盛在石柱周围的那些野花野草,虽无名却香随影动,风姿绰约,信手采一朵,未及鼻前,已被充满野气的花香泌醉了。更有野枣,随处可见,青碧累累,间或又闪出点点的红来。
站在石柱前,旁顾四望,不得不让人感叹大自然鬼斧神工的奇妙造化,不由感叹人类的渺小,感叹人类有时过多的狂妄。身处大自然的怀抱中,竟然想改造大自然。就像坐在树枝上的人,妄想锯掉树枝一样,结局往往会先伤及自身。
稍事休息,一行人顺着石道人山南坡的蜿蜒小路下山,进入北道村。
从北道村到岸青村
北道村西不远有片山楂林。树稀密有致,山楂果正是深红之时,灯照上去,红得更是夺目。树下还算平坦,确为一块好营地,于是决定宿于其下,开怀畅饮。酒意上,累意消,人就活跃起来。
那天是八月十七,十五月儿十六圆,十七更圆似日前。四人餐罢,不舍睡去,于是走出山楂林,步于山道,赏月看景,蓦然发现,原来这一天之来的劳累,就是为了此时之美妙夜景。
且不说,秋意渐深,山风徐来,爽间夹有温意。且不说,田禾正收,四望宽旷,夜色浸满禾香。只说那明月,高悬于东南之天,澄澄清明,朗朗夜界,尽在一片金黄中。南望是山,在山下剪出连绵之势,险处已剪为温和,绵处更描为软柔。一波一波,起伏而跌宕,层叠而融合,以一抹黛色之水墨,泼一幅江南之水彩。北望依旧是山,白日翻过的石道人山,此时已经融在夜中,估计那九名道人也累了,在这月间睡去,人自然与山势融于一体难以分辨。近处的山,却因了月光,更加突兀和鲜明。高的峰凸凸凹凹,更显得挺拔,低的谷却没了棱角,逾显得深黝。最好看的是满山的柿树。树已经掉净了叶子,灯笼似的柿子,在月下呈了黄而透亮的光,似有烛在柿内燃亮,晶莹剔透,似羞怯,更含情,让这山与月更加生动起来。还有无边的秋虫,或啁啾在漫漫山坡,或低鸣于路边草丛,此起彼伏,更为这静的画面添了活的意境。世界便在这夜间,在这夜里10点的秋里,活了起来。
早上8点从营地西行,约一公里许,在古道向北拐弯的地方,就是小有名气的“修路碑记”了。我坐下来,一字一句地抄写着碑上的文字。经过了这么多的风风雨雨,这文字大都还清晰。但也有个别的,或残损,或惨淡,已经无法辨别了。加之还是文言文,其语法语意与今不很相通,有些字词,只弄了个一知半解,还有的,只能用通假或多意的记法,暂时记下来,留待后考了。
大体文字录于此(标点是我整理之后加的):
朐西皆山也。其北道西偏,岭壑尤深,崎曲难行。崖(此字不清)之上出崇霄,下临无地,难系人迹,只有鸟道。实乃地僻天堑,又被水冲激,难通往来。而且侣偻提携往来不绝,常见颠仆之祸,即今思,古蚕农路险犹通车马,丹障峻极而开于五丁,即天设地造亦人力所为也。况此太平峪至西通益境,相连杨集,东即朐邑,直达五井。岂可坐视不顾,大家共议修补,虽不能作为康庄,暂为羊肠。以成,将临村输财,勒石刻永垂千古(今)不朽。
李廷训1千,杨集庵1千,三角地2千,上关省2千,中关省5百,下关省2千……
中在中华民国六年又二月上浣之八日榖旦立
石匠:刘信长 强同云 强怀玉
石碑之处:前二杆 东西四杆 施主王玉节后二杆 施主
碑文甚难辨认,但我弄明白了一个地名,就是北道村所处之谷,叫做太平峪。
沿攀山路绕行崖上,人又进入森林中。这是大片的槐林,漫山遍坡,细密高大,遮天蔽日,纵是秋阳正高,这林中依旧凉气逼人。秋风急来,早黄的槐叶簌簌而落,一地金黄。又被璇来的山风夹起,人就如同沐于黄金叶之中了。
走了半小时才走了这片槐林,差不多已经进入“漫散无人区”的腹地了。路越来越窄,左边是峭壁,右边是大片的槐树、松树,深不可测。在我们到来之前,这里还是一片人迹罕致的纯自然天地。树自然地生长,花自由地开落,草从容地荣枯,还有一些蚂蚱、蟋蟀等草虫,它们愉快地跳来爬去,在他们自己的天堂里,释放着它们生命的最真。现在,总感觉其实我们是多余的,我们的到来,打破了这里固有的原生态的和谐。
在树林中绕来绕去,过了双崮顶,就进入大片的松林了。山上山下,除了树还是树,松林密布,依稀风雨不透,各种鸟鸣响成一片,愈显得这片森林的安静。走在这片松林间,处于悦耳的鸟鸣中,呼吸着夹杂松香的清新空气,心胸一下变得澄明而清透。此时谁也不想说话,也不敢说话,生怕一句轻轻的话语,打破此时山林鸟人和谐共生的那种安宁。
前行约3公里,路已经转到山阳,沿小路,在林间石隙中转折急下,就到了岸青峡谷。这是一处未经开发的自然峡谷。两边,是突兀高出的峰岭,谷底是一条山溪,这时已经没有水了,溪底没有沙土,赫然是整片的石板,估计溪水含钙比较高,溪内的石头已经成为乳白色。
谷内树种颇多,常见的为黄栌、大果榆、五角枫、栾树、连翘、野丁香等,还有一丛丛的无名乔木和灌木,让山谷更是生态自然,层次多样。此时黄栌才要转红,在山悬上拥簇着,五角枫己经闪出了红颜,大果榆和栾树已经由绿变黄,只有连翘,依旧是坚定的青色。
顺谷而下,就到岸青村了。岸青村共有上、中、下三个自然村。三村相连,依山势筑于峡谷内。村庄极富山村之特色。岸青村是极好的美术写生基地,村里路边不时有或三三两两或成群结队的写生者,也不时有行装各色的游人走过,或悠闲地慢荡,或匆匆地急行。但不管什么样的姿态,走在这样的山村里,心情一定是舒展而散淡的。
走在岸青村里,脚步一定要轻松,心情一定要舒展,甚至目光也要缓慢,只有这样,才能看到路旁小溪边,突然闪出的一丛秋菊,或者是一株状若虬龙千态百姿的老柿子树或老核桃树。然后还会看到,村妇安然地坐在门口,摆弄着一堆玉米,小孩子跟在一条狗后面,悠闲地穿过小桥。还会看到,村内的山崖上,山泉正哗哗而下,尝一口,泉水甘甜,掬水在手,清凉爽心。
这时才会发现,世俗的肉体在这里,变得很轻很轻,甚至一阵风来,就有可能随风而去,只留下一颗自由轻松的心,陶醉在这山色之中。
从岸青村到洞顶村
跨过下岸青村西的仁河桥,就是杨集了。在杨集村吃罢迟到的午餐,从村南的小桥西转,是往洞顶村去的路。据说,由杨集去洞顶,只有这一条路。小溪曲折,小路蜿蜒,可惜此时是枯水季节,小溪内的水流极小,在石块的掩遮之下,断断续续。但偶尔从石隙间泛出的溪水,虽细小,依旧清澈明净,爽冽剔透。
路在山谷间,两侧是崖,高不见顶,石块在崖壁上犬牙突起,大有坠落之势,让人不敢多看。崖总连着峰,一个更比一个高;峰总有树,在密林绿叶的掩映之下,更显得苍茫雄奇。还有各种不同的红叶树:黄栌树、火炬树、五角枫,还有一些叫不上名字的灌木荆丛,早红的已经红成一片,晚红的尚半树青黛半树红。还有石,或青灰,或褐红,或灰黄,或五彩相间,在周边山上,在红绿的树丛下,突然就一片片、一块块显出来,与那些红叶绿叶交映,与西照的阳光相映,与更远的蓝天相映。山就活起来,顺光的,五彩缤纷,奇丽秀美。逆光的,被剪出各种形状,或欲奔走,或欲跳跃,或在沉思,或在静卧。每走一步,就是一种不同的色彩,每走一步,就是一处不同的景色。
路边还有众多的杏树,树干苍虬扭盘,树叶小巧而盛绿。可惜是深秋,如果是盛夏,此时就可以品尝那些野杏的美味了。还有山桃,却是结得小而硬,估计是多年未改良的品种,除了做果脯,估计没人肯品尝了。路边自然有野酸枣,这些山里最常见的刺棘树,此时正挂了一树透红之果,摇曳在风中,晃亮了我们的眼睛。摘来品尝,这香甜的、微酸的可口,让我们忘却了一路的劳累。
从杨集步行7公里多,夕阳落山,我们也来到了洞顶村。洞顶村居于皇姑顶上,海拔800多米了,是青州海拔最高的村。营地是洞顶村前的一小片场院。虽弹丸之地,却极为平整。场院两面是近百米的峭崖,从场院边缘,突然就直直地削下去。因为劳累,大家都没了第一天晚上的兴致,吃过饭,就早早钻入帐蓬进入了梦乡了。早晨醒来已经8点了,却还没有阳光的明亮,及至钻出帐蓬一看,才知道原来四面正大雾弥漫,在悄然间,就把洞顶的另一种美,呈现给了我们。
雾从营地的崖下,或缓缓飘上,或急急涌出。总感觉与平原是不同的,这是一些有灵气的雾。知道每一座峰的爱好,知道每一棵树的取舍,知道每一栋房的喜厌。它们或急动,或缓移,或上升,或散碎,把现实的一切,都演绎得如梦如幻。在这样的幻景里,突然发现,原来雾是不动的,活动的,是雾里雾外的一切,是山崖树木山石村庄,以及我们的思绪。
远处的峭壁,已经不见其险陡,只有那些峰恋半隐半现于雾里,随着雾气的飘动,舒展着沉重的腰身,在雾的间间隙隙中,拿捏成不同的姿态。近些的山峦,已经成了雾气里的舞者,在浓浓淡淡的雾搭成的舞台上,或摇首,或摆尾,展示着另一种生机。树当然是更加活跃,伸展着枝枝杈杈,拉扯着,拖拽着,好象要留下这雾气一样。村庄依旧罩在雾气里,偶尔有鸡鸣狗叫从村子里传来,却因了雾气的遮拦,显得更为旷远,像是来自远古的神秘之声,动人心弦。
然后才回过神来,发现有几丝调皮的雾气,竟然缓缓从身边飘过,甚至在脸上戏谑地抚一下,挠一下,在人还没有回过神来之时,又悠然远去。它们缠绵至极,与远处的山,与近处的树,与身后的村庄房屋,若即若离,亲近着,嬉闹着,把清晨的洞顶,扰得生动起来。
洞顶村所处之地之所以叫黄姑顶,据说是因村西潭溪山风景区(属于淄博市辖区)内的昭阳洞而来。此时这个景区还在建造中,沿窄窄的山路援壁而行,一侧渊深不见底,只见林海荡荡,风光无限,一侧紧临峭壁,洞穴重重,美人洞是其中较大的洞,长约百米,可洞穿山体。仙人桥由一巨石横坠于两峰之间形成,宽不足一米,长约三米,深达百米,桥下深谷幽幽,树林密密,行于桥上,令人胆战。过了仙人桥,就到了昭阳洞了。据说这是明朝昭阳太子修行之地,皇姑心疼侄子,随行照料,故此地名之皇姑顶。
据村民们说,漫散古道其实是从洞顶村后一直向西到淄川的。但因时间所限,我们的古道之行到此告一段落,然后返回洞顶村,再往东北方向穿行到黄花坡树,从黄花溪源头顺流出山,返回潍坊。
三天,约70公里的行程,在绿色的丛林中一路追随“漫散古道”,与树为伍,习惯了依树而歇,习惯了树下扎营,习惯了荫下小憩,不知不觉中,这树也成了生命的一部分。坐上回程的公交车,恍忽依旧行走在绿树和鸟鸣中。
森林中的“漫散古道”啊,你让人着迷的不仅是沧桑的历史,更多的是绿色的行程啊!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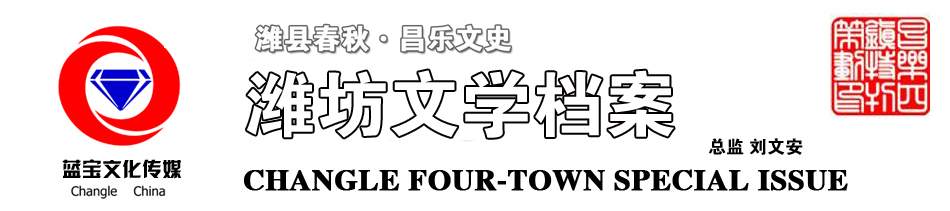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