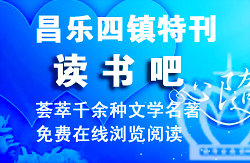
一个热爱文学的人,必定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一个善良、文雅有味道的人,一个对生活有更多思考和体验的人,一个有良知有警醒有责任的人。写作,能自我愉悦,也能愉悦他人,更能让世界变得灵性和丰富。
【昌乐作家专栏】
文学专栏定制:sinoat@163.com
|
吴明金《逸趣斋诗文选》
序——缘分与慰藉
新闻作者:王庆荣
日前,我县退休干部吴明金新著《逸趣斎诗文集》,由中州古籍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作者系红河镇红河村人,原昌乐特殊教育师范学校党总支副书记,2007年7月退休,酷爱文学、京剧。他近十余年来尝试文学创作,作品多次在《潍坊日报》《中国蓝宝石之都·昌乐报》《宝石城文艺》《齐都文苑》等报刊发表。该书收入了作者创作发表的多篇诗词、散文、谱牒,充分展现了其多年来在文学创作方面的成果。
《逸趣斎诗文集》的刊行问世,大可不必用“文苑盛事”“诗坛奇葩”等等半官场的浮艳词汇解读。因为所有在大自然的天光地气中绽放的花朵,皆是应时而生,应运而生,应情而生,应对自然的无条件信仰而生。已与花甲岁序作别的明金先生,以一支书写了数十年公文的笔,撰写出了他作为一种开启性收获的诗文集,无疑是一件有较大社会意义的人生乐事。
作为明金先生的朋友,作为诗文集的第一个读者,我为他高兴,也为我有这样一位年到古稀而不辍其志的朋友而庆幸。从他的诗文中,我仿佛悟出了面对岁月不再为之困惑的真谛和谶语,毅然推拒了被先贤王羲之所摒弃的“虚诞”和“妄作”。人生原本就应该俯察万类,充满阳光。
我与明金不是发小,相识的时间谈不上悠久。但前些年到台湾旅游,天作之合,我们俩同居一室,从那时起我就知道他也喜欢诗词。以心理分析学的观念而言,这种喜欢绝不是一种偶然或突然,而是一种先天赋存的心理能量积累。这种能量,无时不在寻求机会予以展现和抒散。假如这种强劲的内蕴能量早些年得以抒发,或许明金今天已是一位诗坛名宿,一位许多诗人的老师。而长期公务员生活的束限,使明金的诗情画意一直推延到天下升平的今日,才如涓涓流水,得以与惠风和唱,与青山相映。
从内容上来看,诗文集以诗为主,以散文随笔为辅,搭建起了一个健康明朗的心理与情感空间,让文雅和坦诚从字里行间潺潺流泻。对世俗生活的感悟,对自然风光的歆羡,对人文景观的赞叹,在明金的诗文中各有春秋。记得与明金谈论起他幼年捕捉野狸的诗句,仅仅一句“石阳岭上捉野狸”,便勾起了他对童年生活甜蜜动情的回忆,我们一起陶醉在无须强化记忆也永世不会忘怀的大幸福大快乐之中。弗洛伊德说过:“一篇作品就像一场白日梦一样,是幼年时曾做过的游戏的继续,也是它的替代物。”作为一个成年人,乃至老年人,“它可以将今日外表上严肃认真的工作和他小时候做的游戏等同起来,丢掉生活强加在它身上的过分沉重的负担,而取得由幽默产生的高度愉快。”就这一点而言,透过明金的诗文,读者可以看得明明白白。
说到作诗,无论是古体诗、近体诗还是竹枝词、打油诗乃至快板、顺口溜类的民间杂诗,押韵是必须的基本要素。只有押韵才能朗朗上口,易于吟诵,生发诗的特有韵味。“有韵为诗”,这个古今中外达成共识的概念,并不难理解。正如西方的邦维尔在《法国诗学》中说的:“我们听诗时,只听到押韵脚的一个字,诗人所想产生的影响也全由这个韵脚字酝酿出来。”邦维尔对押韵的评价,朱光潜先生认为:“这句话对于中文诗或许比对于西文诗还更精确。”我甚至认为,没有押韵,便没有诗的节奏,没有诗的基本构成原件。
当然,随着历史的演进,语言的韵味不断变化,诗韵的演化革新也是历史的必然。历史上的平水韵形成于南宋,流传影响至今,其艺术精粹毋庸置疑,其中的不合理也显而易见。现代人作旧体诗,应该把韵押到今天的音韵上来,才能化古为今,弘扬传统,给予古老文化以鲜活的生命力。
至于“东与冬”“鱼与虞”“箫与肴”等等诸如此类的所谓不同韵,多已被今人不屑;再如“同与江”“圆与魂”“开与杯”等等诸如此类的所谓同韵,今人也似乎难以相从。钱玄同在《新青年》中曾经尖刻地批评:“故意把押‘阳’‘康’‘堂’这些字中间,嵌进‘京’‘庆’‘更’这些字,以显其懂得古音‘阳’‘庚’同韵。全不想你自己是古人吗?你的大作个个字都能读古音吗?要是不能,难道别的字都读今音,就单单把‘江’‘京’读成古音吗?”
至于格律、平仄,是一个衡量标准争议较大,相对较为复杂的话题。试想古体诗不调平仄,如“关关睢鸠”“枯桑鸣中林”,一句全是平声;又如“岁月忽已晚”“利剑不在掌”,一句全是仄声;你能说不是好诗吗?何况辨别平仄的标准,从来就只是一个受时空条件等多种限制、很不容易达到准确统一的概念。我们清楚,格律诗的艺术价值无可贬斥。但今人切莫专意留情于此,使朱熹老先辈“葩藻之词胜,言志之功隐”的叹息成为传世之忧。千万不可因追求形式而失去言志的激情,使诗作成为规矩平整、兴味寡淡的空架子。
以上关于诗的几点浅见,是我与明金经常的话题。对待押韵、格律、平仄的看法,明金与我略同。仔细想来,明金约我写此文,大致出于这个原因。我之所以欣然领命,也是出于这种对诗词认识的通感。
诗文集中还辑录了明金为《红河吴氏家谱》撰写的文章。谱牒文化通常虽不计入文学艺术范畴,但也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支系,是民族史学文化的三大支柱之一。在寻根热风靡全球的今天,谱牒文化已经显示出无可替代的号召力和凝聚力。对一部诗文集来说,吸纳谱牒文化入编,无疑是别开生面,锦上添花,有容乃大。
读读《逸趣斎诗文集》,体味一下明金先生的花甲文韵,古稀才情。愿与文友们切磋。
后记
新闻作者:吴明金 发布时间:2016-11-04 查看次数:16 放大 缩小 默认
诗对于我来说,并不陌生,儿时就受到堂叔的教育和影响。从“少小需勤学,文章可立身。满朝朱子贵,尽是读书人。”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到“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等等先人名句,皆耳熟能详。上小学时,就爱好文学,特别爱看小说。凡是能找到的小说,不管是古典小说还是当代小说都看,对唐诗宋词尤其着迷。晚上,在小煤油灯下,看到很晚,早上醒来两个鼻孔都是黑的。
虽然年轻时读过不少诗,但对于写诗,却连想都不敢想,总感到诗很神秘,很难写。特别是诗要求讲平仄对仗,要押韵,要合乎韵律。因此,望而却步。
退休后,没有了工作上的压力,解除了思想上的负担,有了充余的时间,也有了闲情逸致,开始尝试写点诗歌。2013年4月,昌乐县作协原秘书长朱彬占同志组织郭建华、王庆荣、徐振田、徐士祥等同志去台湾旅游,我与王庆荣同居一室。对王庆荣的名声早有耳闻,只是未曾相识。这次通过交谈,他对诗词方面造诣颇深,受益匪浅,大有相见恨晚之感。回来后,在彬占和庆荣同志的鼓励下开始文学创作,并向报刊投稿。令人高兴的是,竟被采用。当时的心情,激动得难以形容。于是,一发而不可收。
对于写诗,我感到首先应以立意为主。诗是一种最普遍的艺术,如阳光洒落在人类社会的每个角落。鲁迅先生曾经说过:“诗是韵文,从劳动时发生的;小说是散文,从休息时发生的。”所以我们说,诗是普遍的艺术,是一种最为古老的文学艺术形式。诗是艺术的语言,也是语言的艺术。诗最本质的特征是抒情美,无论是小说、散文、戏剧,最优美之处,无不闪现出诗的光环来。因而,诗是文学中的文学。在艺术领域中,诗无所不在。诗美是艺术美的普遍因素的最高体现。诗能净化心灵,陶冶情操,提升人的思想境界,增强审美观念。诗言志,要把自己的感情通过诗的形式表达出来,使之形象化、具体化,给人以美的享受。因此,就不要过分地去追求平仄对仗。当然,对于律诗的要求也无可厚非。
这本集子,主要辑录了近几年来在报刊发表过的文章。大体分三个部分,一是诗词,二是散文随笔,三是谱牒。去年我参与老家红河村的族谱续修工作,并担任主编,给我提供了一次极好的学习机会。通过修谱,使自己增长了不少历史知识。所以,将有关文章一起录入本集子内,以供读者参阅。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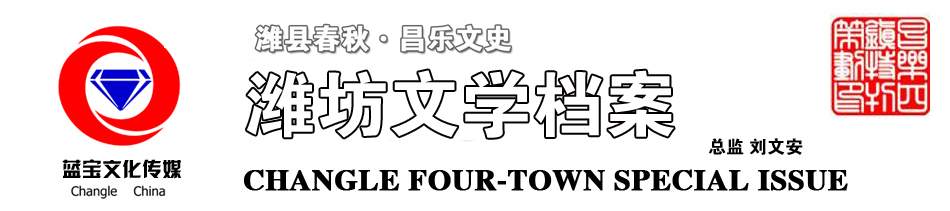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