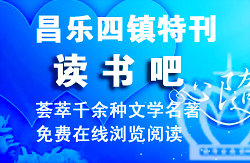
一个热爱文学的人,必定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一个善良、文雅有味道的人,一个对生活有更多思考和体验的人,一个有良知有警醒有责任的人。写作,能自我愉悦,也能愉悦他人,更能让世界变得灵性和丰富。
【昌乐作家专栏】
文学专栏定制:sinoat@163.com
|
绝世美味,人间烟火——安丘美食之芝泮烧肉
作者:李风玲
绝世美味,人间烟火——安丘美食之芝泮烧肉
清晨,一声渺远的鸡啼唤醒了沉睡的村庄。五月的风,沾染着麦子的香,在晨光熹微中吹过绵延的绿树红墙。
沾染着露水,沐浴着霞光,我们一行四人,来到了位于安丘市东部的这个古老村落——景芝镇芝泮村。早在明朝万历年间,这个村落就因为一道菜而名扬四海。它就是芝泮烧肉。传说在乾隆三十八年(1723年),刘墉之父刘统勋病故,刘墉正任陕西按察使,回家奔丧。在回陕之前去其姑家(其姑家就住芝泮村),其姑送其本村特产烧肉10斤,刘墉带至京城,乾隆帝品尝后赞叹不绝,龙颜大悦,当场挥御笔书写“芝盘留香”四个大字(因乾隆将“芝泮”误以为“芝盘”)。据说乾隆书写此四字的资料记载曾经有在北京工作的安丘乡人于北大图书馆查到,但这四个字并没有得以流传,实乃遗憾。
走过久远的历史,如今的芝泮烧肉已经不仅是一道菜,饕餮着安丘人的舌尖,它更像是一缕情,绵延成游子的乡愁。究竟是怎样繁杂的工序,让一种滋味醇香绵厚,又究竟是怎样传奇的秘方,让一种传承历久弥新。带着这些疑问,我们走进了村中70多家烧肉加工户中的一家——刘家。村民们都说,他们家的烧肉加工,颇为传统,也颇为正宗。
刘大哥和刘大嫂都是特别爽朗的人,对于我们的突然造访,他们略带羞涩但充满热情。我于是有幸见证了芝泮烧肉的制作全程。
日出而作。刘大嫂为丈夫扎上围裙。一天的忙碌就从这小小的动作中,温柔地开始。
霞光初露,空气清新,院里的蔷薇吐出新蕊。
房子是前几年才盖的,足够宽敞。庭院。堂屋。正房。但每天早晨,只要一起床,刘大哥和媳妇儿的活动范围便仅仅囿于整个院落和南屋的灶间。一年365天,他们都要在这片不算太大的天地里让自己的劳作实现色、香、味的完美蜕变。
比刘大哥更勤劳的,当是附近的屠户。他们早早地就送来了猪头和下水。十几只白白的猪头在案板上排列整齐,很有些气势。它们在等待下一步的工序。十几副下水也分门别类在各色的盆里,等待清洗。如果逢上中秋或者春节,这十几副猪头和下水也将供不应求。但无论市场的需求有多大,刘大哥始终坚持着自己做烧肉的数量和质量。慢工出细活儿,古老而传统的家庭工艺尽管有些追不上现代文明的步伐,但那份正宗的滋味儿,却让一代又一代的芝泮人心甘情愿地恪守传统,咂摸其中。
朴实的刘大哥性格开朗,整天乐呵呵的,一副喜庆模样儿,媳妇儿对他颇为依赖,宛若他的跟班儿。小两口儿夫唱妇随,本本份份地做着自己的烧肉,不偷功,不减料,多少道繁复的工序走下来,那味道,自然就有了。
今天的猪头很新鲜,刘大哥相当满意。
拔毛是第一道工序。镊子在手,刘大哥动作娴熟,娴熟而细致。从鼻孔到眼角,每一个毛孔,他都要照料到。一个个猪头在他手里宛若珍宝,几番雕琢过后,更显其珠圆玉润。
刘大嫂也没闲着,她在清洗大肠儿和小肠儿。刘大嫂笑容憨厚,性子也绵柔。生活中,丈夫就是她坚实的臂膀,大小粗细,皆可仰仗。但唯独清洗猪下水的活儿,每次都是她亲力亲为。她说,洗肠这活儿,考验的不仅是体力,更是心力。
卤水斩豆腐,一物降一物。肠们在盐水的刺激下杀了性子,但每天三遍的搓洗依然相当劳神费力。但无论怎样的繁琐,刘大嫂也绝不会有丁点儿的偷工减料。只有最咸的汗水,才能腌渍出世间美味。
炉火烧起来了。很旺。这滚烫了十几年的老汤锅在刘大哥的调理之下,保持着一如既往的沸腾。
烧火棍被岁月打磨的锃亮。通进灶底的一头焊上了钢铁的方块。可别小视这些钢块,它们一方面要很踏实的护住炉底,让火势永远旺盛不息;另一方面,它们还担负重任:给猪头和猪蹄祛除油灰。
烧火棍已经通红。刘大哥轻轻地抽出一根,双手紧握,烙向案板上的猪头。有条不紊,细致均匀。
空气中弥漫着烧烤的诱人香味。脸部,嘴巴,耳朵,在火块的炙烤中,猪头由白变黑。刘大哥动作从容,语言却朴素而幽默。他说,猪生前可是从来不洗澡的,为了卫生,在做成食品以前当然得好好的清洗一番。于是,这烙去油灰就显得尤为重要。
太阳渐渐高起来,刘大哥的额头沁出密密的汗珠。其实随着时代的发展,很多的烧肉制作人已经改用喷灯给猪头祛油。但刘大哥说,喷灯烙的虽然快,但味道差的很远。所以,他宁愿累点,也要用最原始的方法做出芝泮烧肉的本来味道。
猪头烙好了。表面的焦黑之下,包裹的却是本质上的洁净。
新一轮的清洗又开始了。刘大哥移动着手中的钢丝球,擦拭着猪头被炙烤后的黑色。
猪头被还原出本色。这次,它们白嫩的更加纯正,由标至本。
刘大嫂也已经齐活儿。
十几副猪下水,五个小时。如今,它们肝是肝、肺是肺的躺在属于自己的盆里。盆里的水清清白白,无比清澈。盆内之物也再无半点腥臊。
院子里满是缸缸盆盆。红塑料大盆,椭圆木质盆,黑色泥陶盆,它们大大小小、或古朴或现代的陈列在院子里,干净卫生,各司其职。
万事俱备。刘大哥开始磨刀霍霍。
猪头劈开了。照例是三瓣。刘大哥将它们一一浸入老汤锅。石头和铁质的箅子让肉与汤的相容更加浑然一体,彼此相依。
看看灶底。火势正旺。
簸箕端出来了。在一味味中药的敲击研磨中,它苍老了自己的容颜。豆蔻,砂仁,肉桂。花椒,八角,茴香。这些婉转而古朴的名号,给芝泮烧肉的制作,添加了画龙点睛的一笔。但传统而又朴实的芝泮人,从来不把它看作什么秘密。在他们看来,即便告诉所有的食客芝泮烧肉的秘方,他们做出来的烧肉也绝对不是芝泮村的味道。因为无论是用料的多少,还是火候的把握,都需要时间的历练、经验的积累,而在历练和经验之外,更要有一种对食物的天生敏感。当这一切的因缘际会聚合在一起,这锅肉,才算是上好的美味。厨房的秘密最终是没有秘密,而这没有秘密,得经过滴水成珠的岁月的熬煮。
撒几粒枸杞。这是刘大哥的别出心裁、推陈出新。这一颇具匠心的小小细节,给注重养生的现代人,增加了一道健康的砝码。
很多在外的安丘游子,如果过年不得回乡,便经常想方设法自己动手做烧肉。凭着记忆,也凭着想像,自己鼓捣配料,放在大锅里熬煮,但费尽心机,却终不是家乡的味道。这时的烧肉,已经不仅仅是一味菜肴,更是一枚家乡的符号。这枚符号,饕餮着安丘人的舌尖,也绵延了游子的乡愁。
肉已下锅,炉火正旺。
刘大哥终于可以忙里偷闲,坐在马扎上抽一支烟。戏匣子打开了,唱的是《小姑贤》。带着乡土气息的朴素唱腔里,小两口儿享受着片刻小憩。刘大哥记起今儿个是周末,外出求学的儿子会回家晚餐。这让他很是兴奋。和妻子悠闲的对话里,多了些慈父的表情。一只苹果被刘大嫂咀嚼的有滋有味,看似无心的问答里,充溢着女人的温顺和满足。窗台上的小花伸长脖子,偷窥这夫娼妇随的甜蜜。
袅袅升起的烟圈里,刘大哥瞅瞅院子里的表:肉该出锅了。
揭开锅盖。热气腾腾。香气扑鼻。不油不腻。
三个小时。大火与文火的有序交替,大概只有煮了十几年烧肉的刘大哥拿捏的最为有度。
撒一勺白糖。再将锅盖,盖个严严实实。这甜丝丝的滋味,将为夫妻俩一天的劳作,做最后的封笔。
下午六点,正宗的芝泮烧肉,出锅。热乎乎,香喷喷,油而不腻。门外已经站了不少的买客。一盘刚出锅的芝泮烧肉,将是他们晚餐桌上的重头戏。
“烧肉一嚼,才叫生活。”熏风乍起里,来一盘“凉拌猪耳朵”。雪白的香葱,脆绿的黄瓜,透明微红的猪耳朵,谱成一篇写意小品,装点着夏日黄昏。在视觉与味觉的双重盛宴里,我们享受其中,欲罢不能。
俗话说,“一级烧肉不出庄,二等烧肉下了乡,三等烧肉集上卖,四等烧肉精包装。”夕阳西下,吃一口刚出锅的烧肉,是刘氏夫妻对自己的最大犒赏。在这个古朴的村落,在这个传统的家庭作坊,这一桌正宗的芝泮烧肉,当是至鲜至仙的绝世美味,却又是实实在在的人间烟火……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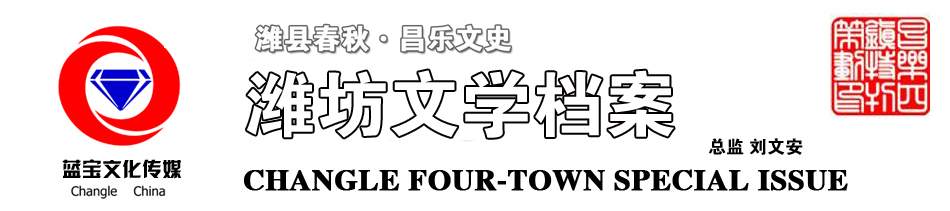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