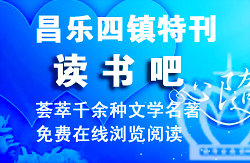
一个热爱文学的人,必定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一个善良、文雅有味道的人,一个对生活有更多思考和体验的人,一个有良知有警醒有责任的人。写作,能自我愉悦,也能愉悦他人,更能让世界变得灵性和丰富。
【昌乐作家专栏】
文学专栏定制:sinoat@163.com
|
闲话厕所
作者:郭建华
闲步街头,一座建筑物在我眼前一亮。驻足观看,是一间新建的厕所,主体已经完成,建筑工人正在安装管道。厕所的外观颇为时尚,与周边环境也很协调,竟像是一道不错的风景。据了解,这样的公厕在县城分布着很多个。看着这风景,脑子里不由得翻箱倒柜,把一些关于厕所的零零散散的碎片尽数抖搂出来。
儿时家乡的厕所,称之为“栏”或“圈”,如厕则叫做“上栏”或“上圈”。染了肠疾,频频如厕,则说“跑栏”。厕所之所以叫做“栏”,与其功能有关。彼时农家的厕所是与家畜之圈合二为一的,如牛圈、羊圈、猪圈等,猪圈最为普遍。圈的格局大多一棚一池,棚为挡风遮雨,池为沤肥攒粪。二者都是为家畜所谋,如厕倒像借家畜的地盘,钻家畜的空子了。之所以如此“反客为主”,是出于那一池粪肥的宝贵。在化学肥料尚未普及中国广大农村之时,农家就指靠几池粪肥打发那几亩庄稼。这一过程长达千百年。到了大集体时期,化肥已普遍使用,但粪肥仍不可或缺。一则粪肥为有机肥,肥效长,肥地且养地。二则化肥要花钱购买,而粪肥仅靠人工和家畜即可获得。生产队日子紧巴,但人力不缺,故而尽量选择后者。一般每户春秋各攒一栏粪。出栏之后,要堆放得四四方方,由生产队派专人以皮尺丈量,计算出数量,然后评估定级,确定质量,最后综合质、量两方面,给粪肥定值,即记工分。工分相当于内部使用的货币,有“工分儿工分儿,社员的命根儿”一说。猪既是造粪的机器,又喜欢在圈池内踩踏翻拱,于圈肥的沤制极为有利,故是否养猪直接关乎粪肥的质量。猪因此也有一份额外的待遇,卖掉之后,按毛重记工分。两栏粪、几头猪在社员的收入中举足轻重,因而家家户户都十分重视养猪,当然也就十分注重猪圈的修建与维护。
后来卫生部门大力推行改厕,即圈、厕分开,层层发动,奖惩并举,频频检查,典型带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历经数载、甚至十数载,厕所总算在农家院中有了一席之地。为便于将粪便排于圈内,所建厕所仍与圈相通。厕所貌似独立,实际上仍是圈的附属。
再后来,圈的功能渐次衰微,直至名存实亡。原因是养猪走向规模化、集约化;农民种大棚瓜菜,也是整车整车地从养殖场购买猪粪、鸡粪。猪在农户、甚至整个村子几近绝迹。猪既不存,圈有何用?农家的厕所这才真正获得独立,越来越像厕所了。
农家厕所身份的变化,仿佛给中国农业文明千百年来的曲折发展划出一条若隐若现的轨迹。
城市的厕所让我大开眼界,惊异地发现厕所竟然会是这般模样。第一次惊异发生在孩提时代。叔父带我去济南,走出火车站不远,便看见一溜房子,低矮而狭长。奇怪的是,窗口开在屋檐下,极小,门口则在房子两端。一位老头儿守门,不时有人出出进进。进门者将零钱交与老头,换取一张草纸,然后做解腰带状。我问叔父:这是什么地方?答曰:茅房。上茅房怎么还要花钱买纸?我大惑不解,近前看,却见老头儿守着小炉子,炉子上坐一砂锅,热气腾腾,里面正煮着面条。我更加大惑不解:茅房门口怎么可以煮饭?叔父说:里面很干净。我怎么也无法将这所奇怪的房子与厕所联系在一起,满腹疑团,一步三回头地跟随叔父离开。
时隔近三十年,我方识得这种城市厕所的“庐山真面目”。1985年,我赴上海参与潍坊电视台出品的第一部电视剧的拍摄。其实大上海的公共厕所比较稀缺。每到一处外景地,合作方上海电影制片厂派出的剧务,便悄悄侦察附近单位可供使用的便池(一般设在院内隐蔽处,简陋狭小但清洁,仅供内部人员小便之用,管理不严,故外人偶可“借用”),及时告知剧组人员。这天,剧务告诉大家:今天有公厕,就在对面里弄,很近。一脸的得意。我走进对面里弄的那间公厕,第一感觉就是宽敞明亮,一尘不染,毫无异味。便池为沟状,流水潺潺,清澈见底。管理人员身着工作服,戴橡皮手套,穿水靴,极从容、极专业地冲刷擦洗,一丝不苟。外面下起雨来。路人陆陆续续进厕避雨,收起手中的雨伞,静静地看着雨急雨缓,也有相熟者唧唧哇哇,聊着聊着就有笑声暴发出来。看来,这种避雨方式、避雨场所,上海人早已习以为常了。蓦地,我想起了济南火车站前卖手纸、煮面条的老头儿,儿时的困惑烟消云散。
我惊异于上海人做事的认真和精细,一间公厕竟然建造得如此,又管理得如此整洁宜人。他们怎么想得出、又做得到呢?该是文明程度所致吧?我向往上海的文明,自公厕始。
十余年过去,公厕文明的迹象在我的家乡显现。家乡最文明的所在,莫过于县城了。小小县城,公厕还是有几座的,但如厕却不易。厕内之脏臭,不便描述,归结起来,有三不敢:不敢走、不敢看、不敢喘气。这一年,县城突然兴起“公厕热”,数月内,几乎该有公厕的地方都建起新公厕,而且像模像样,就外观而言,不逊于我所向往的上海公厕。内部也装备了冲水设施,且配备了管理人员,大可与上海公厕媲美了。县城的市民和进城的农民跨越式地享受到了公厕文明,惊喜、惊叹,无以名状。
前不久看到一条消息,称某县出台新规,为方便群众如厕,县城所有机关单位内部公厕一律向群众开放。消息曝出,立刻引发热议。褒之者说,关注民生,此举可嘉。贬之者则斥为“作秀”。窃以为,是否“作秀”大可不必细究,只要这新规有效,且为长效,这一创意就值得肯定。至少,衙门敞开了,哪怕只有窄窄的一条缝。百姓进入,不必再接受冷言厉语的盘问,甚至须出具介绍信、身份证等等有效证件,岂不是一大进步?何况还能堂而皇之地解手方便。迈出这一步,新规制定者需要有何等勇气!自然,此举也难免有“亡羊补牢”之嫌。如果县城有足够的公厕,且布局合理,又何必发文颁规,请百姓进机关如厕?想必此城“翻盖”之时,规划师和设计师也将公厕这一元素忽略或遗忘了。正所谓吃喝拉撒,衣食住行,乃人之本性。如何吃喝拉撒,什么样的衣食住行,则体现人之文明。眼下,开豪车、住别墅、海参鲍鱼、奇装异服,即使在县城,也非罕见,罕见的倒是公厕,岂非咄咄怪事?人若随地方便,岂不等同动物?城市不设公厕,岂非让人向动物看齐?果真如此,我们离文明将何其遥远?
如果说农家厕所的演变,勾勒出农业文明的轨迹,那么,城市公厕的设置和完善,则是城市文明进程的标志,至少是标志之一。看一座城市的文明程度如何,不妨先看看它的公厕。
“亡羊而补牢,未为迟也”。一座座崭新的公厕终于在街头现身,终究是一个令人振奋的好消息。它至少证明,城市文明的提升,又迈出新的一步。
上一篇 下一篇
版权所有:昌乐传媒网 未经授权禁止复制或建立镜像 昌乐传媒集团平面媒体中心编辑室:6801056 备案号:鲁ICP备10206506号51.La 网站流量统计系统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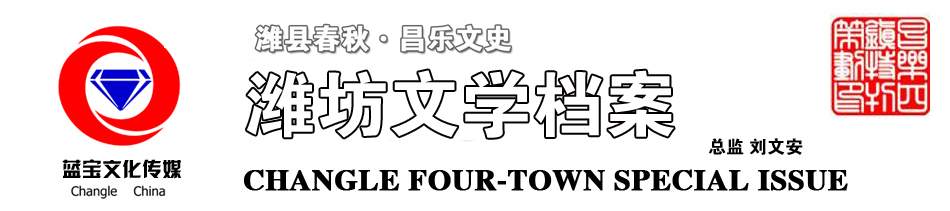
![]()